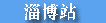首页<<远程教育
寻找将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
更新时间:2012-2-26
寻找将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
早在几年前,陆续有出版社找我,说要出版我的论文集,我都婉言谢绝了。我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虽写过一些文章,编过一些书,主持过一些课题,但还谈不上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去年(2008年),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与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组织编辑出版新中国教育学专家自选集《中国当代教育论丛》,将我的论文自选集列入选题计划,不久就确定了论文集目录初稿。我觉得这本论文集是对我自己几十年来求学、治学的一个小结。趁此机会我谈一点自己的感受, 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我的求学之路
我是一个农家子弟,1934年12月15日出生在河北景县的一个小村子里,父亲是个普通农民,七岁时,和村里大部分同龄孩子一起,被父亲送到了小学读书。实际上,这所小学是个半私塾性质的,是由私塾改良而来的,老师就是原来的私塾先生,对新式教学法一知半解,糊里糊涂,后来从县里派来的新式师范学堂毕业师范生代替了老秀才,体育、音乐课程也像模像样地开设起来。家长对他们的到来以及新的课程、教法很摇头,我们小孩子却喜欢得很。
此时尚处于抗日战争当中,我老家的地区属于那种叫做拉锯战的地区,白天是日本鬼子和伪军的天下,晚上就是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的天下。我上的小学就是“两面小学”。日本人、伪军来扫荡了,我们就拿出那种日本人发的书应付一下;他们走了,我们仍旧念的是八路军、游击队发的书。
小学毕业后,因为县城没有初中,我投考了冀县和南宫两所县级初级中学。我的运气不错,两所学校都上榜了。但当两张录取通知书真正送到家里的时候,大伯却坚决反对,说读的那些书在农村完全派不上用场,还不如早点长点本领。父母觉得大伯的话很有道理,便决定让我跟从舅舅学习木匠活。
正当我准备做木匠学徒的时候,一场洪水却成全了我继续读书的梦想,突如其来的洪水将地里的庄稼冲个精光,家里粮食顿时紧张起来。这时候,每个月有60 斤小米供应的初级中学待遇,就有了相当的吸引力。家里人一合计,大伯最后拍板决定,“吃你那60 斤小米去吧”。我选择了冀县初中,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离家相对较近。冀县中学不是完全中学,只有初中部。按照老解放区的模式,采取配给制,每月的60 斤小米一半用作膳食,一半作为服装、文具和日常用品开支,家里不用出钱。就这样,从初中开始,我便开始在国家资助的情况下读书,不再花费家里一分钱,实际上家里也没有那样“闲钱”供我读书。在旧中国,对于一个“一贫如洗”的农家孩子来讲,没有钱而能进一步读书绝对是“连想都不敢想的”。所以,我常常半开玩笑地讲,我求学经历本身就是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是各级政府严格贯彻“教育向工农大众开门”方针的受益者。
初中毕业时,我们这种配给制的学校被要求只允许报考中等技术学校。此时父亲才去世,身为家中长子,从情感和责任上讲,我都希望自己能早点挣钱养家,我选择了河北省建设学院财经部(后改称河北省保定财经学校,以下简称财会学校),学习会计专业,学制两年半。1955年1月,我以全优的成绩,被分配到石家庄地方国营棉织厂,在财务室做出纳工作。工作刚几个月,厂里要精简行政人员,而当年高考生源不足,国家鼓励社会青年以同等学力参加高考。就这样,厂里默许我们几个年轻人在不耽误工作的情况下“备考大学”,8月份,我居然收到了北京俄语专修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的录取通知书。
1955年9月,我背上简单的行李,来到北京。俄院当时设有一部和二部。一部是培养国内紧缺的俄语教师和翻译专门人才;二部即为留苏预备部,专为准备留苏和留东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准备,在校进行一年的俄语和政治学习。我进入的是一部,四年制师范翻译系,学校聘请了一部分教学经验丰富的苏联语言专家担任我们的教师,苏联专家鲍米诺娃、马蒙诺夫、毕丽金斯卡娅等人先后到校任教,我们也或多或少听过他们的课。后来由于人员不足,又从当时在北京工作的苏联技术专家的家属中聘请了一部分人来讲课。
1957 年,中苏两国关系渐趋冷淡,不仅留苏预备部的辉煌不再,当年在留苏预备部学习、准备出国攻读大学本科的学员,全部没有派出;我们一部也受到了牵连。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培养大量俄语人才已不再成为国内急需,当然也就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师资力量,按照上级指示,要对一部进行紧急“瘦身”。当时我们那一届有六百人左右,学校动员我们转学,到更广阔的天地贡献我们的力量。当时,我可以选择北大、人大、师大等在京高校文科专业,经过比较,我选择了北师大的教育系。
9月份,我进入师大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学习,1961年我在教育系本科毕业时,学校正在筹办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我“服从分配”进入研究生班继续学习。
就全国范围内讲,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的开办不是首次,在50 年代初期和中期,华东师范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分别在孟宪承先生、王逢贤先生等主持下,先后开办了两个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但规模都较小,只有一个导师,如华东师大招收了5名学生,全部师从孟宪承先生,即李国钧、孙培青、江铭、张惠芬和郑登云,培养出的“五虎上将”,毕业后全部留校工作,极大充实了华东师大的教育史学科的力量。这次北京师范大学开办的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算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办这样的班了,但与前两次相比,具有招生规模大(20 人)、名师集中、培养人才多的显著特点,在当时具有不小的影响。
就我本人来讲,我是不情愿进入研究生班再继续学习的,一是家庭比较困难,想早点工作;再者觉得自己老大不小了,因为我是工作一年多考的大学,且是读了六年大学,应该工作了。但是,从学校到系里,都反复动员我,最后直接说进研究生班学习是组织上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服从组织分配,进入了研究生班继续学习,担任班长。
研究生班采取导师制。当时北师大教育史教研室的五位教授,除去邱椿先生以年岁较大拒绝带学生之外,瞿菊农、邵鹤亭、毛礼锐、陈景磐名下各分了4—5人,我被分给了邵鹤亭先生。上课方式是大课, 按照教育史历史的传统分段,每位先生以自己所擅长或感兴趣的部分,从先秦两汉一直到近现代,系统地讲,有点类似历史系上通史课的课堂教学模式。
就当时学习来讲,没有什么教材,不是不指定,是根本就没有,国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1961年4月,在周扬的主持下,教育部会同文化部共同召开了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形成了《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学方针和教材编选工作的报告》。随之,教育部专门召开了一个全国文科教材建设会议,教育学科中的“中国教育史”被列入教材建设的重点教材,还成立了专门的教材建设小组。会后,教材建设小组按照学科优势,将“中国教育史”教材编写任务做了一下大概分工:按照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历史分期,由四所学校编写两套教材,发行全国。北师大独立承担一套教材,包括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要编三本教材。为了编选好这套教材,6月21日,陈垣校长邀请范文澜、翦伯赞、林励儒、邱汉生等著名专家,就教育系中国古代教育史编写组拟定的“中国古代教育史”大纲举行过座谈会,集中讨论中国教育史教材编写中的一些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老先生给我们班上课时又增加了一个目标,将编写教育史的教材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会议后,研究生班的培养目标慢慢发生了转移,不再单纯学习中国古代教育史,而是根据教材编写的需要,近现代教育史都要学习,这样,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生班的名字被逐渐淡化,后来就直接称为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
为了完成教材编写的任务,老先生们的主攻方向进行了一次调整:邵鹤亭、瞿菊农、毛礼锐三位先生,负责中国古代教育史教材的编写,相应地中国古代教育史课程也重点由他们三位来上;陈景磐先生则重点承担中国近代教育史教材和课程;由于这些老先生中没人专门搞过中国现代教育史,现代教育史的课程一度搁浅。后来专门从中央教科所聘请了陈元晖先生(后长期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由他来承担教材现代部分的编写,同时为研究生班讲授该部分的课程。按照学生研究专长和兴趣,重新调整了导师,拨出两个学生分给了陈元晖先生,我和何晓夏跟从陈先生学习中国现代教育史。
在研究生班期间,感触最深、收获最大的就是在老先生指导下读了不少书,在图书馆抄了不少书,先后手抄过《古今图书集成》、《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著名书院志、蒙学读物、小说笔记和地方史志等近400余万字。通过抄写保存了文献资料,加深了记忆,锻炼了意志,还感悟出不少治学修身的道理。这些资料的积累,为我的治学探索之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研究生班读书期间,我们赶上了“四清”运动,我们由三年毕业也就变成了四年。先后两次“四清”,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等我们再次回到学校,已经离1965年暑假、离这一届毕业生毕业时间有三个月的时间。学校觉得也不好再推迟我们毕业,就要求每人都交一篇论文,没有履行答辩程序。就这样,我们结束了四年研究生班生活,匆匆忙忙、稀里糊涂毕业了。
可以说,我的求学之路上有太多的巧合,是一个又一个带有偶然性的巧合凑在了一起,构成了我长达二十余年的求学生涯。从高小到研究生,自然环境可以成为继续读书的理由,小到风吹日晒,大到天灾(发洪水);国家教育政策、工厂内部调整可以成为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国际环境和外交关系也曾改变过我的求学方向;国内的政治运动也和我的学生生涯扯上了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无论高小,还是冀县中学,还有我的六年大学生活,四年的研究生班学习等等,好多事情都是自己没有办法把握的。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讲,面对这些,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以坦然的心态,接受不能改变的,然后将事情尽可能做好。
二、我的学术探索之路
1976年10月底,我从教育系调到北京师大文科学报做编辑。1993年10月,我又被调回到教育系做教师,在学报工作了十七年,事实上,十七年中我始终没有放弃所学专业,一直在教育系兼课,协助老先生搞科研,带研究生,并自己主持科研项目,招收研究生。只是在教育系不记工作量,不拿任何报酬,被认为是“吃学报的饭,给教育系干活”,几个获奖成果都是在学报做编辑时完成的。1993年调回教育系之后六七年,在教育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还一直兼做学报编辑工作,变成“吃教育系的饭,为学报干活”。我深感,在高校学报做编辑兼职承担一定的教学科研工作任务,教学科研人员兼职承担部分编辑工作,是大有好处的。
1978年6月,我在学报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四人帮”批“智育第一”是对德育智育的全面破坏》。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命题作文,还带有那个时期特有的色彩,还算不上什么学术论文。实际上,除去本职工作,我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上。1980年4月,在学报发表了《论“学而优则仕”》,这应该算是我真正意义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在文中,我提出“学而优则仕”思想本身具有明显的两重性。在对待“学而优则仕”的问题上,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已经表明,遵循这条原则,就能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违背或破坏了这条原则, 就必然阻碍甚至毁灭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在今天看来,是很平常的,但就当时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来讲,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学而优则仕”说成是所谓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精神支柱之一;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的人常常把“学而优则仕”作为批判的重点,说它是没落奴隶主阶级教育路线的核心;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的人也常常批判“学而优则仕”,它说成是封建教育的灵魂;“学而优则仕”被视为没落的、反动的教育思想,似乎仍然是一种定论。我提出这种观点,被不少人称之为“胆子够大”。其后,我就“孔子教育思想的阶级属性”、“孔子教学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孔子的德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简明中国教育史》编写中,我也承担的是前两章的撰写任务。在《中国教育通史》中我还就“《吕氏春秋》中的教育思想”作了挖掘等。
1980年5月下旬,陈元晖先生找到我,将一份古代书院的撰写提纲和几十页发黄的讲义交给我,希望能整理、扩充成为十多万字的书稿。历经一个暑假的挥汗如雨,终于形成了十二万多字的书稿,从书院的起源、书院的教育内容、书院的管理特点以及对今天教育的借鉴等来论述古代书院,陈先生看过很满意。该书稿次年以《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为书名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我署名第三),有研究者认为“此书奠定了书院研究的基本框架,开启了新时期书院研究的先声”,我认为有点过誉。大概是由于此时发表学术论文、出版专著者还比较少,特别是像我这个“中青年人”,在不少人眼里,我便成了研究书院的专家。其后,和李国钧、李才栋教授合作主编中国《书院史》,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的《中国古代书院》,陈学恂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宋元分卷》(我和郭齐家教授任分卷主编)中宋代书院部分也自然落在我的头上。近几年来,我也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论述书院的文章,我一直认为书院留给后人最珍贵的是书院精神,而书院精神是书院教育在长期发展历程中不断积淀和凝炼而成的优良传统的结晶,是书院办学传统的灵魂。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变革,书院制度的存废,书院办学型制的变异,时有发生,而书院精神却是永存的,自然成为中华民族教育遗产宝库中的珍贵财富。每当酝酿或推行新的教育变革时,人们往往会打开教育历史遗产宝库,获取智慧,寻求启迪和借鉴,并将前人的智慧和经验,运用于教育变革的实践中,在运用中进一步丰富和创新,而这进一步的丰富和创新,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又逐渐沉淀和生成新的优秀历史传统。书院精神久为人们关注,并在历次教育变革中得到传承和创新,丰富了内涵,增加了生命活力。这也是我一直关注书院研究的最基本动力所在。
“十年浩劫”结束后,伴随着中教育史研究的重新探讨和对中国教育史地位的正确估价,中国教育史课程在高师教育系的地位得到了恢复并加强,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教育史教材,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毛礼锐先生多次对我讲,“能有一部通史,对于了解中国教育发展史的全貌,把握中国教育发展史的基本线索和总的特点,探索中国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十分必要的”。编撰卷帙浩大的通史提到了日程。毛礼锐先生提出组织力量编撰《中国教育通史》的建议,但老先生们大多年老体衰,“心有余而力不足”,急需年富力强而有较强组织能力的科研梯队的加入。从1983年开始,我作为毛先生的助教, 协助毛先生组织力量投入研究,先后参与人员五十余人,分散在全国不同的院校、研究所,从1985年《中国教育通史》的第一卷问世,直到1989年六卷本付梓,其中所耗费的气力决非笔墨所能描述。因审稿工作大多由我和国钧教授捉刀,老先生们或重病在身,或精力有所不及,大量的组织及拿给老先生们看后,然后“子以令诸侯”。在此期间,《中国教育家评传》(三卷本)也得以完成。
《中国教育通史》先后获得第二届吴玉章奖金一等奖(1992年)、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95年)等荣誉,得到学术界很高的评价。也常有人讲我为《中国教育通史》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我总是报以一笑了之。我常对学生讲,我很自豪我一直担任毛先生的助教,直至1992年毛先生去世。此时,我自己已是博士生导师,但在老先生的面前,我依然是助教。这个过程是一步一步跟从老先生学做学问的绝好机会,有机会在老一辈先生的指导下,做成一些事,收获很大。我愿意始终抱着兢兢业业、诚诚恳恳的态度,在科研的道路上延续老先生们的遗志,并尽可能将其发扬光大。正是有了这个机会,我结识全国教育史研究界的众多朋友,逐渐积累了与人合作的经验,为90年代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中国教育思想通史》是一部规模较大的学术性著作,被列入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中华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全书由我和河北大学的阎国华教授担任总主编,各分卷主编是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队伍,基本上是在《中国教育通史》的队伍基础上加上青年一些骨干组成,担任本书各分卷主编和撰稿人中的大部分成员已有近十年合作研究的基础。从1989年动议,到1994年6月八卷本复梓,期间先后在重庆、呼和浩特、兰州等地召开过全体编写组的会议,邀请专家参与讨论,大家集思广益,框定编写原则,分卷主编各负其责,大概在1993年三四月份,稿子大体完成,我便开始找寻时间,“周游各省”,在各分卷主编处看稿;最后一站是到保定,和阎国华教授汇合,交换意见,确定进一步修改的方向。全书定稿时290余万字,被称为“迄今卷帙最为浩繁的中国教育史论著。因其巨大的篇幅空间,在内容安排上做到了广收博采,展现了中国教育思想发展的丰富多彩的特点”。1994 年6月出版后先后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二等奖、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不少参与其中的青年人开始崭露头角,锻炼了队伍。
当我们完成《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的编写任务之后,曾想着手开展“经学与中国传统教育”的课题研究,并且邀集了几位年轻学者进行了多次商讨,还草拟了一份研究计划和大纲。后因忙于《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的编写,更由于深感研究这个课题难度极大,信心不足,未敢贸然出手,只好暂且搁置了。然而研究的愿望和冲动却时时萦绕脑际,总想寻找机会尝试一下,后来,学生米靖的博士论文曾在“两汉”这个时段作了有益探索。就整体来言,经学与中国传统教育相始终,还有很宽广的空间需要研究。
在此期间,我还应山东教育出版社之邀,主编了《中国古代私学和近代私立学校研究》一书,该书由我的两个学生吴霓和胡艳的博士论文组成,我只是撰写了序言,该书获得了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在此基础上,1996年增加力量,申报了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国家教委重点课题“中国私学、私立学校和民办学校研究”,历时8年完成,2004年结题。我一直认为,古代私学和近代私立学校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厚的客观社会基础,统治阶级的政策导向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私学和近代私立学校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也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这一点,需要我们认真总结。
《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完成不久,山东教育出版社找到我,希望能编写一套制度史,我起初有点犹豫,原先做思想史的主编们大多到了退休年龄,组织一支新队伍谈何容易;出版社同时也在力邀李国钧教授出山,他也有和我相同的顾虑。出版社很执著, 我向来不善于说“不”,国钧也已经被说动,我们便“老夫聊发少年狂”,组织队伍,再担重任,开始给中青年学者压担子。这是一支较年轻化的队伍,青年人思路开阔、敏捷,勇于创新,不大容易被条条框框束缚,但他们还缺乏必要的积累,需要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历练。《中国教育制度通史》被列入了国家新闻出版署“九五”重点出版规划选题,1998年年底基本完稿,全书331万余字,2000 年7月出版,先后获得了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等。该书的撰著出版,是大家历时多年通力合作的结晶。
早在90年代初,国家教委决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的研究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的重大课题,何东昌同志为牵头人。总课题组下设了若干子课题,我承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的历史传统与基础”子课题,还担任总课题组的学术顾问之一,参与“国史”的研究、编写工作。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教育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有着一些惨痛的经验教训,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总结经验。
对于科举制度研究的关注,无论是中国教育思想史还是制度史,都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课题,我发表了几篇文章,主编了《中国科举制度研究》一书。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现代高考制度反思的深入,科举制度被作为高考的远祖,被纳入或为批判或为之翻案的“风口浪尖”。我也经常被各种杂志、媒体盛情相邀,谈一些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科举考试制度是历史的产物,从酝酿和萌芽、形成和发展,从逐步完善到日趋衰败,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地位、作用和影响是不断变化的,对它的评价应该有所不同。大体说来,隋唐、两宋利多于弊,得大于失;元、明、清逐渐转化,特别是明中叶后至清末,显然已经是弊多于利,失大于得,最终走向衰亡。我们不能以对科举考试制度在某一发展阶段利弊得失的考量,做出对科举考试制度的整体评价,更不要以对前期的考量否定对后期的考量,反之亦然,这才符合历史主义的原则。
从2004年开始,以厦门大学潘懋元、刘海峰教授等为发起人,每年召开一次“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年会,迄今已有六届,他们邀请了不少历史、文学等专业的研究者,还有海外研究科举的知名学者,强调从多维角度来研究科举制度,我认为很有意义,值得我们教育史的学术年会借鉴,不能是自家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要请相关学科的研究者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有分歧、有争论不是坏事,去年(2008年)在保定的学术年会有所改进,首先应该在这个方面加强努力。
就教育史研究来讲,无论思想史还是制度史,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在国家教育体制内的学校教育,尽管在《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各卷中对社会教育(传统社会称之为社会教化)作了一些努力,但明显还不够。我国历朝历代重视“化民成俗”的传统以及形成的一整套体系,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整理。2004年,我们启动了《中国社会教育通史》,已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出版。《中国社会教育通史》的编纂基本集中了北师大的教育史教师力量, 是“211”重点项目的课题。目前,各卷正处于紧张推进之中,计划于2010年适当时候交出初稿。
从80年代开始,我对传统文化与教育现代化问题就比较感兴趣,发表了一些文章,也尝试着做一点研究。2006年6月,以“中国优秀教育传统和创新研究”为题,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教育学科)2006年度国家重点课题,我是总主持人。该课题基本上以所里的力量为主,加上我已经毕业的几个学生,共分为七个子课题,我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北京大学教育评论》上发表“书院精神的传承和创新”和“承与创新:从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到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两篇文章,作为这个课题研究的一点进展,也算是“身先士卒”吧。近年来,我越来越感觉到组织大型课题困难,这种合作的大项目非一朝一夕之功,很难短时期出效益,每年的计量考核逼迫研究者不得不“单打独斗”,做一些“短、平、快”来满足年终考核,分散了很多精力,难以拿出有分量的东西出来。这个问题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从2005年3月开始,我被学校委任为《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史》的主编,由王明泽、孙邦华、李敏辞、徐勇任副主编,周慧梅担任我的助手,开始编撰师大的百年校史。2007年12月,近一百万字的初稿初步完成,先后召开了两次不同范围的意见征求会,校史撰写原则虽是“专家撰稿”,但就本身性质来讲,却是“官方修史”,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写组先后三次集中通稿,就各自负责的章节逐章修改。目前,我正在看第四稿,已经统了四分之三,准备暑假再集中一次,就可上交给编委会了。
作为一个高校教师,我认为,最本职的工作还是教书。我喜欢上课,喜欢和年轻学生在一起,我马上就75 岁了,多年来,不管科研任务多么繁重,我一直坚持每学年给本科生上一门课。我认为,对于大学来讲,本科生的教学质量更值得关注。我担任过两年学校的本科生督导团组长的工作,每周深入到本科生课堂去听课三节,和其他督导团交流,大家都感觉本科生课堂教学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一些教师对待教学的态度值得重视,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倾向,当然这也和高校目前的考评制度有关。我一直认为,科研是为教学服务的,是要围绕教学进行、要和教学能相得益彰的,而不是为科研而科研,和教学是“两张皮”。多年来,我坚持将学术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在教学中延展学术研究,感觉效果不错。如从2004年开始,我在北师大教育学院开始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的公选课,至今已经坚持了六年,学生反响很好,而且数年积累的教案已基本形成了教材模样,正在作进一步整理。2006年12月,以我为申报人“中外教育史专题”被列为硕士研究生基础课程建设项目,实际上,该课程是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所一直开设的课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作为“21世纪高等学校研究生教材”中“教育学专业系列教材”由北师大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该书分为四编21个专题,是大家科研和教学结合的一个典范。6月份,我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十佳共产党员”,学校组织部录制记录片时,我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声,我深深热爱我的教书岗位、育人事业,“愿意再为党工作十年!”
三、我的一点感悟
改革开放30年来,我每天都很忙碌,很充实,主持过一些课题,担任过一些社会兼职,作过两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教育组)成员,主编了几个大部头的通史和资料汇编、几本学术刊物,就一些教育问题发表过一点自己的看法。选入本文集的多是散见于各种杂志、书籍中自己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篇章,还有一些序言和发言稿。将文集定名为《寻找将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实际上是我的老师陈元晖先生的一贯追求,我之所以借来作文集的名字,主要是想说明我所做的事只是将老先生的事业继承、继续下来,同时,也希望能薪火相承,青年学者能将教育史学科发扬光大。
这些年我听到了很多关于对教育史的各种声音,其中有无奈和沮丧的,也有欢欣鼓舞的。我总在反复想着一个问题,我从事了五十余年的教育史研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借此机会就这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实际上,教育史面临的问题不是近年才发生的。如大家常讲的教育史研究生就业困难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生毕业时,就已经出现了。按理说,北师大培养的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生,当时不论就业形势如何严峻,也不至于有人找不到工作吧。就业难的背后,一是由于教育史的专业性质问题,一是政治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教育史属于基础学科,由于学科性质,难以和实践结合得多么紧密,1965年全国都在大力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联系,由于大家老觉得研究历史是搞老古董,没有现实意义,所以凡是牵涉到历史这个学科的,都是被一再一再地压缩,本科生教育史课程的学时越来越少,原来学校里面有一个老师能做教育史的老师,那就足够了,不会补充新的教师。这个问题在今天还没有得到解决。
90年代至今,我一直担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史学科规划组成员、组长,对教育史的学科定位、发展、队伍建设、学位点的建设、研究生培养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应该说,这三十多年来,教育史学科的发展算很不错,甚至可以说超出了它的正常发展,在学科积累的资源方面,这三十年来发挥了很充分的作用。我们可以作一个比较,我们这个学科在20世纪初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支建立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差不多也就是四五十年,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也差不多有三十年,合在一起,教育史出的成果连我们现在研究著作的三分之一都不到,甚至四分之一都不到,我们现在的教育史研究机构多了,培养的人也多了,每年都有那么多硕博士生毕业,就这个学科本身承担的任务来说,已经是超出了正常的状态了。
面对中国教育史面临的各种问题, 我常常借用胡适先生“鹦鹉救山火”来形容这种心情。记得2006年在古城西安召开的教育史研究会第九届学术年会大会闭幕式上,面对会议期间大多青年教师、学生对教育史学科的困惑、迷茫和无奈情绪,如课时遭到压缩、在学科中被“边缘化”、不受重视,申报课题不易、学生分配困难等,轮到我发言时,我说给大家讲个故事,“森林着火了, 里面居住的动物一边向外逃,一边抱怨,怎么这么倒霉。一只鹦鹉却匆忙往返于溪流和森林间,将自己的翅膀沾上水,飞到着火的森林上空,将翅膀上的水抖落,一次又一次,尽管尽可能小心振翅,但每次能运回来的却是寥寥,甚至只有几粒水珠。面对动物们的疑问,鹦鹉这样说,‘我知道这样做无济于事,但求心安。’ 我这么多年一直从事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对中国教育史学科存在的问题、大家讲到的体会很深。我现在能做的,就像那只鹦鹉,停止抱怨,能做多少做多少。”我的话音刚落,掌声雷动。我知道,掌声的背后有的是客气,但我更愿意理解为“所见略同”,或是引起了青年学者、学生的共鸣。事后,有好多青年人跟我讲起,当时是如何受到触动,我感觉很是欣慰。
我常常在想,教育史学科依然面临着尴尬状态是与其学科性质、定位有很大关系的。大家说教育史怎么重要,但实际上却没有重视,因为上面没人说还是没有用,我们多数情况下还是听上面的。其实呢,谁心里都知道教育史挺重要的,搞教育学科的,哪一个学科都离不了教育史;搞其他教育学科的,他要是学过一点教育史、注意一点教育史、愿看一点教育史,这对他来说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于有些搞其他教育学科的人,做研究的时候,他自己知道他的短处,他对教育史太不了解了,尽管如此,教育史还是不能成为一个热门的专业。
我们看待、评价一个学科,很容易受功利性影响,要求这个学科面向教育现实,如果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就认为这个学科有价值,有地位,如果没有发挥作用,就没有价值,这样看待这个学科,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导向。在现实中,我们常有意无意地强调学科能够影响和参加国家教育发展的重大决策和现实问题的解决能力;还有是“生搬硬套”、“牵强附会”,研究的是教育史,脑子里想的却是现实中的问题,常常出现用历史上的东西来附会现实问题,这是违背了教育史研究最基本的宗旨。教育史不可能和现实性联系得这样紧密,不可能起到主导性作用,最多起的是辅助性的作用,我们要立足一个基础学科,为所有的教育学分支学科提供一个基础,这是教育史的基本宗旨之一。另一个是教育史学科是为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研究者提供一个基本素养,而不是帮助他解决什么根本问题。如果我们立足这一点,教育史学科就会很主动也很轻松,也不用担心被人怎么看不起,就不会再妄自菲薄,说教育史学科萎缩了啊什么的。其实搞教育工作的人,不管是理论工作还是管理工作、实际工作,都是需要教育史基础的,这样就够了。总要求它发挥多么大的影响,参与国家教育决策,参与现实问题的解决,那就偏离了教育史学科的基本定位。
所以,与其说教育史专业困惑问题,倒不如说是教育史学科的性质和定位的认识问题。我自己认为很简单,教育史学科是教育学科里面的一个基础学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基本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不是直接追求的目标,而是人们从中得到的某种启发、借鉴,帮助他去观察和思考现实问题,而不是直接去参与现实问题的解决,所以这样就闹出好多笑话,比如孔子的素质教育思想,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又如孔子的和谐教育思想,弄得好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有点启发,弄得不好呢,会觉得简直是荒唐。
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服务的一个领域,不能要求所有的学科都归到一个方面去,这也影响到我们学科的发展。我们感觉作为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教育史学科现在成果很多,力量也已经相当不错了,就想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不很现实,我们自己要心里非常明白,教育史学科它再冷也冷不到哪儿去,再热也热不到哪里去。明白这样的道理,我们自己心里也平和一点,我们应该把能做到的事情做好。也许,像陈元晖先生多年执著探索哲学、心理学那样,是为了寻找将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而我们研究教育史,同样也是找寻那朵将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仅此而已。
在教育史界,由于长期没有明显的学科分化,大家一直以为或致力于教育本身发展历史的研究,而实际上教育史所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一部分是教育活动本身发展演变,大部分却是历代教育家对教育认识的发展演变。因为研究教育活动本身的历史所能够依据的事实十分有限,只能依靠大量前人遗存的文献,而这些文献除直接记录着教育本身的事实之外,更多的是前人对教育的认识。但是这些文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教育活动的真实,是需要检验的,而检验的客观依据又往往是不足的。而一旦将文献研究误以为就是研究了教育本身的历史,常会带来许多不良的后果。对此,我常常困惑。
近些年来,我一直暗自为《中国教育学史》的撰写收集、准备着一点资料。在指导学生们的论文过程中,我对古代教育家的论著进行重新研读,作了不少读书笔记、心得;2008年第二学期,应劳凯声教授之邀,为教育学博士生开了“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历史意识”专题讲座。我认为就教育,史研究领域来讲,前期在教育思想史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为教育学史的研究作了必要的铺垫。换句话讲,不同的教育思想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与发展历程,从而形成思想发展史,其本质是对教育认识历程的记录。从思想史上升到教育理论的发展过程,就形成了教育学史。我以前主编过《中国教育思想通史》,有了这个积累,我对撰写《中国教育学史》还是有了一点底气。
感谢顾明远先生及北师大教育学部其他同事对我的这本集子的选编出版的关心和帮助。我还要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和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的领导魏运华、吕达编审等决定将拙著纳入《中国当代教育论丛》出版表示深深的谢意。
是为自序。
山东招生咨询网(www.sdzs365.com)
热点新闻
教育书籍
热点新闻
招生就业
假期旅行